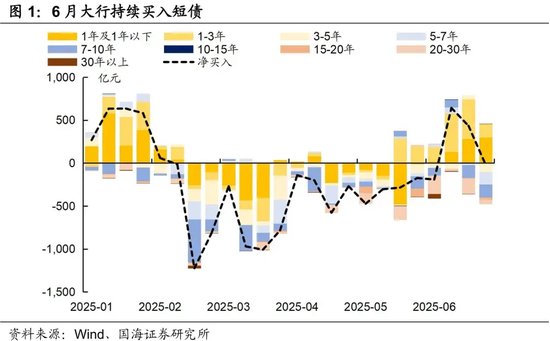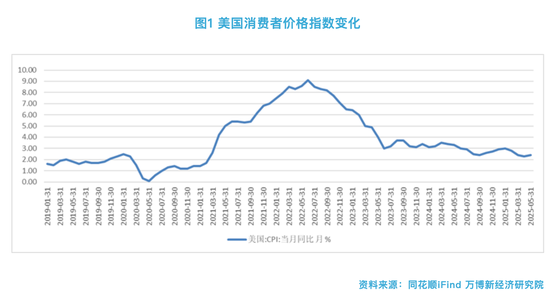高连奎《中国原创经济学》书籍连载
导语:当前经济学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不足之处及潜在缺陷,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创新探索。
——笔者近二十年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
一、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创新
1. 重视经济均衡,忽略经济效率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石的微观经济学,其目标是寻求“均衡”,而非“效率”。然而,并非所有经济均衡都代表着最高效率。均衡状态既可能是高效的,也可能是低效的;它可能出现在山顶,也可能位于山谷。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其经济都处于均衡状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低效率的均衡并非我们所期望的,因为这种均衡通常是在供给无法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提升价格来抑制需求而达成的。若以此为追求,将毫无实际意义。经济发展所应追求的应是提升经济效率,而非仅仅追求均衡。均衡的本质在于供需的平衡,然而我们追求的却是“供需的最大化”,这才是我们的目标,而非仅仅是供需的相等。我所倡导的平衡经济学,正是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并且构建了一套关于如何提升经济效率的理论框架。
2. 重视需求的弹性,忽略供给的粘性
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是以供需弹性为基石,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供给与需求不仅具有弹性,还带有粘性特质,尤其是供给的粘性对经济产生的效应尤为显著。在“弹性”这一假设下构建的均衡理论,实际上不过是空中楼阁。在平衡经济学领域,笔者提出了“供给难度”和“供给粘性”这两个概念,从而彻底颠覆了现代经济学在弹性假设下所提出的均衡假说。以“粘性”理论为基石的平衡经济学,其理论体系与现行经济学截然不同,不仅假设相悖,得出的结论亦必然有所差异。我曾用过一个类比,若将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比作物理学中摩擦力的引入,那么我提出的供给难度概念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便如同重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仅仅探讨“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却忽视了“干预性市场”的运作规则。
作者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自由市场”与“干预性市场”两大类别,这两个市场在运作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
规律迥异,现代经济学专注于探讨“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却忽略了“干预性市场”的运作机制,这导致众多人误以为那些研究“均衡”经济学的权威人士均倡导自由市场。实则,瓦尔拉斯、马歇尔、希克斯、阿罗等构建均衡经济理论基础的大家,几乎都主张对市场经济实施适度干预。其中,贡献最大的瓦尔拉斯更是公开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仅仅是便于研究而做出的一个假设。阿罗亦声称,一般均衡理论基于五组假设,但每组假设从现实角度审视,都存在错误。在当今社会,完全的自由市场已不复存在,市场干预现象日益普遍,例如,在中央银行的调控下,货币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干预市场。这种干预市场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已持续超过百年。与自由市场追求的“均衡价格”不同,干预性市场更侧重于“均衡供需”的实现。所谓“干预性市场”,就是通过价格调整或其他干预手段,力求达到一个“合意的均衡供需”状态,这正是干预性市场的显著特征。
过分重视私人产品的自我平衡机制,却忽视了公共产品领域本身所具有的天然不平衡特性。
现代经济结构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市场构成,其中,私人产品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进行有效调节,而公共产品市场则需依赖其他手段进行管理。
公共产品市场未能达到均衡状态,而其需求受到私人产品的影响,供给则受限于所谓的“税收刚性”,缺乏灵活性。因此,公共产品市场本身就具有一种固有的非均衡特性。在新的财税经济学理论中,我将其称之为“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过分强调私人产品市场的平衡状态,却忽略了公共产品市场的不平衡特性,这种做法是片面的;公共产品市场的不平衡现象是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供应的不足所引起的。
过分关注市场供需的考量,却未能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各类产品间的相互交换。
货币的问世使得供给与需求在时间维度上出现了分离现象,然而萨依早已强调,商品之间最根本的联系是交换行为。因此,若要真正洞察经济实质,就必须摒弃货币和价格等因素的干扰。我所倡导的平衡经济学,正是完全无视货币与价格等干扰因素,直接从生产与交易层面构建的经济运行理论。在平衡经济学中,市场交易被简化为高供给难度产品与低供给难度产品之间的交换。同时,该理论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剩。而通过增加“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不仅能解决经济危机,还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
过分强调产品在技术和包装方面的区别,却未注意到不同产品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其供应的难度。
市场经济通常认为各类产品性质相似,然而存在一些特例。例如,在垄断竞争理论中,特别突出了产品的独特性。然而,该理论对异质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产品技术和包装等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非根本性的。在平衡经济学领域,本研究提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产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供给的难易程度上。由于供给难度各异,各产品的供给效率也随之不同,进而引发市场上不同难度供给产品间交易的不均衡,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
仅仅察觉到市场中假设条件出现了失效,却未能深入探讨“市场核心机制”的失败情况。
现代经济学在探究市场失灵时,关注了信息、交易成本、外部性等因素,却未能意识到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经济的关键机制同样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同样可能引发市场失败。在平衡经济学领域,我运用供给粘性理论论证了价格失灵的现象,指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供给弹性”这一基础,而一旦供给表现出“粘性”,价格机制便可能失效。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存在缺陷,同时,竞争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另一大核心要素,亦存在不足。针对此,笔者提出了“竞争风险累积引发经济危机”的理论观点。该理论指出,市场竞争可能导致市场风险的不断集聚,而在市场竞争最为激烈之际,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此时,市场主体所获得的利润最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弱。一旦市场遭遇突发冲击,整个经济体系便可能陷入危机。审视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几乎都伴随着某一行业的激烈竞争与全面崩溃,进而波及至其他行业,引发整体经济危机。无论是早期的纺织业泡沫、铁路业泡沫,抑或是后来的房地产业泡沫、互联网业泡沫,莫不如此。为此,笔者提出“市场核心机制失败理论”,用以解释由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核心机制导致的失败现象。这一理论区别于以往的研究,以往研究认为市场存在条件失灵是导致市场失败的原因,而实际上,市场存在条件的失灵并不会直接引发经济危机;然而,市场核心机制的失败却足以引发经济危机。
仅对合同要素对薪资稳定性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却未注意到“生活开支”实际上才是造成薪资稳定性的最关键因素。
市场经济遭遇经济危机时,其自我恢复的速度并不迅速,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工资的不可变性。这一观点最早由凯恩斯提出,随后美国新凯恩斯学派的费希尔、耶伦等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他们主要从长期劳动合同、效率工资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阐释。然而,在生存经济学的探讨中,作者强调生存成本是造成工资刚性的核心因素;而长期劳动合同以及效率工资机制,仅能解释在常规经济环境下的工资变动难题;但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些解释显然不再适用。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部分高收入者的薪酬具备一定的弹性,而低收入者的薪酬则难以实现灵活变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受到生活成本的限制,正是这一因素构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工资刚性的核心所在。
9. 重视福利分配,却缺乏生存经济学研究
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占据着核心地位。尽管它已走过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但研究焦点始终集中在不同个体间的资源分配与利益补偿等议题上。在马尔萨斯之外,现代经济学界鲜有人对“人类生存”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此,笔者创新性地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生存经济学构建了收入与生存成本之间的关联模型,并阐述了人类经济发展如何作用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变化。唯有生存经济学,方能从经济学视角全面解析人类生存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中,笔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对低收入群体底层商品市场的完善与构建,以及构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倡议。相较于福利经济学,这一研究更贴近经济现实。
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收入与心理预期之间的联系,却未充分考虑收入与生活开支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当代经济学领域,幸福指数理论同样存在,然而,他们所构建的是基于期望与效用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心理预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关键因素。然而,这种观点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因为心理预期因人而异,难以进行量化评估,所以,幸福指数同样难以被准确衡量。作者构建的幸福指数模型关注的是收入与生活费用的关联,若收入超出生活费用,人们便感到幸福;若收入与生活费用相近或不足,人们则不会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指数体现了唯物主义观点,它不仅可衡量、可量化、可统计,而且能够通过经济或社会政策手段进行调控。
在探讨货币贬值问题时,人们往往仅将通胀因素纳入考量,却未将生活成本增加这一重要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在当代社会,人们普遍感受到货币价值的下降,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所能完全解释的;实际上,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才是造成这种货币贬值感知的根源,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货币的实际价值下降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是相等的。人们普遍希望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然而,伴随经济的增长,“生存成本”持续攀升。因此,在投资理财和经营管理家庭的过程中,为了准确估算货币价值的下降速度,我们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更应将生存成本上升的因素纳入考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个与现实感受相符的货币贬值率。
只关注到国有企业在管理层面的低效表现,却未注意到它们在某些特定领域所拥有的
供给能力强、供给效率高的优势
现代经济学领域内,国有企业常遭受污名化对待。国企与民企的优劣评价,不能仅以“管理效率”这一单一维度为标准,而应采用更全面的供给效率、供给能力等多元指标进行评估。供给效率不仅涵盖管理效率,还涉及资本效率、生产效率等多个方面。国企凭借信用优势,其资本效率往往超越民企。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国企不易破产,在长期投资方面亦占优势。国企拥有组织优势,在“高供给难度产品”领域展现出强大的供给能力,这些都是民企所不具备的。鉴于此,作者提出,应摒弃仅以“管理效率”评价国企优劣的片面观念,而应从供给能力、供给效率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国有企业的价值所在。
过分强调实体经济的地位,却未充分认识到虚拟经济在提升交易效率方面的重要贡献。
经济体系由实体部分和虚拟部分构成,实体部分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而虚拟部分亦同样关键。在凯恩斯学派所倡导的三大经济动力——投资、消费与出口——的理论框架下,对虚拟经济的贡献难以充分阐释。然而,依据我提出的“新三驾马车”理论,即关注生产效率、交易效率以及产品创新,便能够较为轻易地揭示虚拟经济的实际作用。当服务领域涵盖虚拟经济时,其所提供的服务在推动GDP增长方面与其他产品的创新作用相当;此外,众多虚拟经济形式,如互联网电商、社交平台以及金融投融资等,都能显著提升经济交易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不仅能够借助“增强产品创新”这一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能通过“增强产品交易效率”这一手段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
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权利进行了探讨,却未能充分考虑销售者的权益。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主权理念,但销售者的主权观念却鲜有提及。然而,销售者的主权在经济学领域尤为突出,尤其在互联网和服务业领域,这一现象愈发显著。因此,本文作者提出了“销售者主权”这一概念,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依据“销售者主权”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轻松理解为何大量低价商品在市场上逐渐销声匿迹,同时也能解释为何为富裕人群服务的机构数量显著多于富裕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而面向贫困人群的服务机构数量却远不及贫困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
仅从收入层面来分析贫困问题,却未充分认识到底层市场的缺失才是贫困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
现代经济学通常将贫困的根源归咎于收入水平,即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长,但仅从收入层面来分析,依然难以充分解释为何底层贫困依然存在。鉴于此,本文作者认为,底层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商品市场的不完善。这种不完善部分源于销售者权力的过度集中。
低收入人群所依赖的市场正逐渐萎缩,与之相关的产品也逐步退出市场,这种现象无疑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生存负担,成为他们陷入贫困以及贫困问题难以根除的关键因素。若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政策,构建并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础商品市场,众多低收入者便有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无需依赖国家的福利援助,贫困问题亦可通过市场化手段得到有效解决。
导语一: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创新